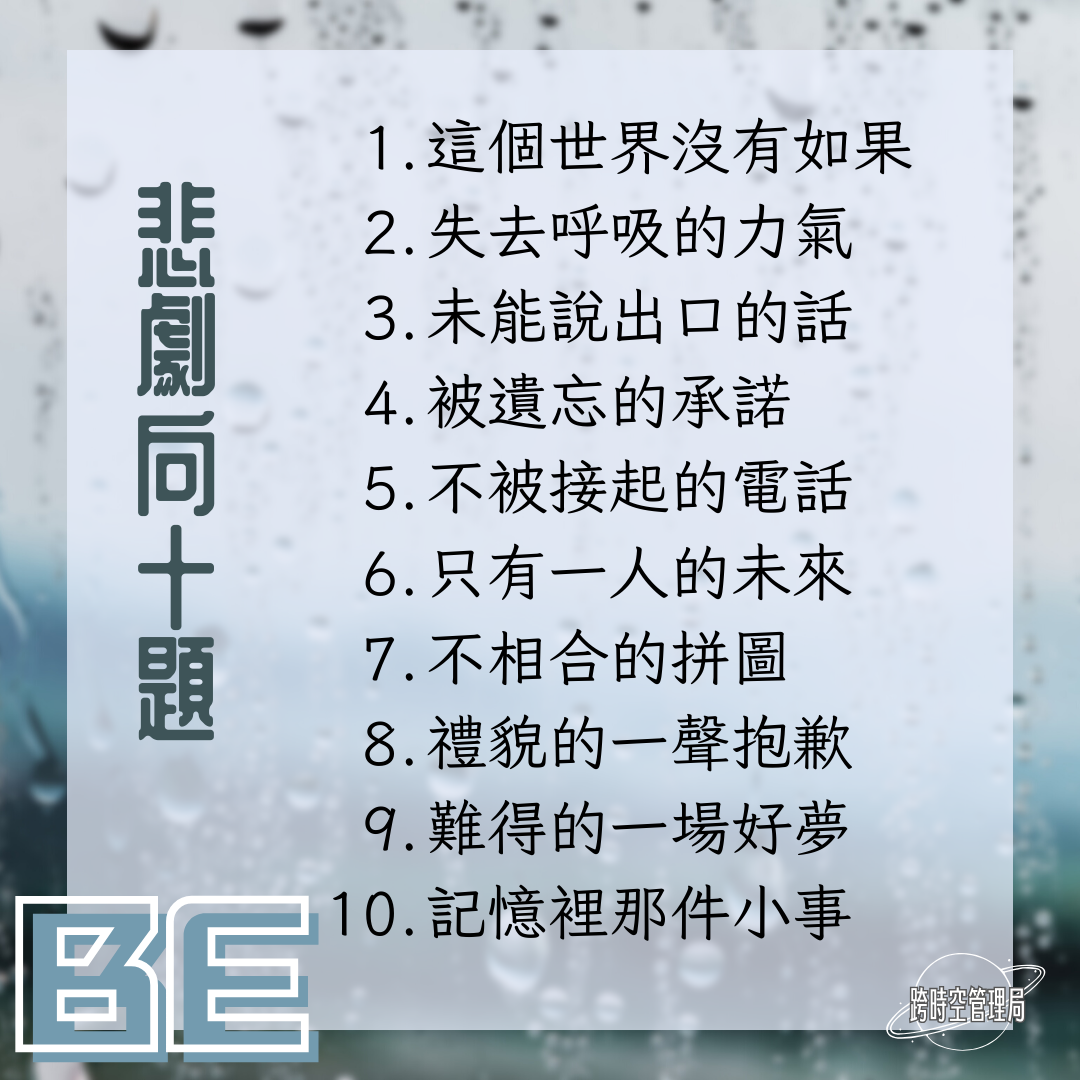2024年1月7日 星期日
2024年1月6日 星期六
2024年1月2日 星期二
【手塚X由衣】新婚十題
1.一起構想房間設計
即使不是在都心,三房兩廳的房子在如今的世道果然也是有些奢侈,
遑論屋子的主人一年內也可能有超過半年不在這裡。
不過以長遠計,由衣選擇欣然接受這樣的奢侈。
有個小問題是除了裝潢,還有家具必須自行添購,說來慚愧,她還真的少了一點點美感。
「這邊整面都規劃成書櫃吧?你覺得怎麼樣?」她一邊翻著各種裝潢與傢俱相關的雜誌、與去新家拍攝的照片比對著問身邊的人。她其實有些後悔提議自行規劃,早知道應該全權委託裝潢公司就好了……
「要滿足這面牆寬度的書櫃必須訂製。」手塚平靜地背出牆面尺寸,「底下有插座,也要考慮。」
由衣其實已經累得恍惚,為了趕在下一次賽季前能趕快開工,他們已經連續討論了數天。
說是討論,幾乎是由衣發表想法,手塚只負責評論可行性。
她疲憊的打了哈欠,隨手揉了下眼睛引來手塚有些責備的眼神,但她已經沒有多餘的注意力可以發現。
由衣在筆記型電腦上打字紀錄著,「那就這個書櫃還有衣櫃⋯⋯跟廚具櫃都找設計師處理,其餘的傢俱就我們自行採購吧。」
匆匆做了結論,手塚凝視著妻子將文件存檔的動作,點了點頭表示默許。
隨後,便各自洗漱然後結束一天。
由衣渾然不知自己的丈夫在夜半又重新開啟了另一份文件。
保留了由衣的想法、完善了由衣未考慮的地方。
還小小添加了一些自己對於「家」的期望。
由衣在看見了那份真正意義上為兩人一起構思的文件後,感動得無以復加也是後話了。
2.新家派對的名單
由衣對於新家派對感到困擾。
新居落成,一般就是找現在的同事、朋友來分享喜悅。
手塚的所謂「同事」如果要邀請還真是大工程,而若是都只有她的同事朋友又總感覺哪裡不對。
當她詢問手塚後,問題迎刃而解。
「找他們來就足夠吵鬧了。」
都不知過了幾年,那些人都已在各個領域有各自成就,甚至有不在國內的人。
可是在這一天仍能齊聚一堂,由衣深深感受到她的丈夫究竟有多受他們的喜愛。
「耶——乾杯——恭喜喬遷新居!」
3.一絲不苟的溫柔
由衣已經連續加了三天班了。
雖然不是通宵,但高強度的腦力工作讓她在踏入家門後,還能記得洗漱後再上床已經很好了。
凌亂的玄關鞋子已經被排好,還多了一雙鞋。
洗衣籃內只有她今天換下來的衣物。
早上她匆匆出門遺留在餐桌上的空杯與空盤此時乾乾淨淨地在水槽旁的瀝水架內。
擺放在房間一角的兩個行李箱。
以及雙人床已經空了一段時間的那一側睡了一個人。
她渾然不知。
感受到身側的溫暖,她僅是下意識地貼了過去,反倒是那人被她嚇了一跳。
手塚今天中午一進家門就知道由衣應該工作忙過了頭。
他盡可能地把看到的家事全部都做完了,原本還有猶豫是否要等待她到家,但時差以及他到家並沒有休息到的緣故,手塚還是在晚上九點這個標準入寢時間上了床。
他一手反射性的輕撫了妻子的頭,又重新閉上眼。
不知道明日由衣是不是仍要工作這麼長時間?
比起和式早餐,或許能夠快速用完的餐點會更適合忙碌的她。
在他重新入睡前想的最後一件事情是他帶回的新咖啡豆,正好適合這時候的她吧。
4.生活採購清單
由衣自認雖然不能算是一個細心的人,但偶爾有些小細節她也常常能考慮得很周到。
比如安排採購清單。手塚在家的時候,她會特地另外寫一張清單給他。
而有些物品——例如女性生理用品、她慣用的洗髮沐浴產品等等,她會另外寫一張清單以提醒自己要再去補足。
但是今天當她從後陽台回到室內,看到兩份清單都不翼而飛的時候她臉上瞬間冒出黑線。
剛剛他們的對話是怎麼樣來著?
「我要出門一趟,妳剛剛說有什麼需要買的?」
「啊,清單我放在桌上,麻煩你了。」
對,是她的錯,因為她寫好兩份之後,聽到洗衣機完成洗衣的聲音就放下筆離開桌前了。
她確實不是個細心的人,也不是個謹慎的人。
一個鐘頭後,她的丈夫回來了。
手塚提回的物品裡,準確無誤的是她使用的衛生棉品牌以及是目前家裡缺少的款式。
她的清單上應該只寫著衛生棉三個字。
「呃,抱歉,讓你買這些是不是很尷尬?」
「沒什麼。」手塚神色淡然,「以後不用分成兩張。」
由衣覺得自己好像很窩囊,因為她有些感動得想哭。
5.轉播裡的人
惱人的鬧鐘聲響起,由衣難得的在響第一聲就馬上按掉。
然後馬上從床上彈跳起來,最快速度打開了電腦連上了賽事直播網站。
好險如今是夏季,如果是冬季她肯定無法那麼快跟被窩分開。
也好在今天是假日,否則比賽結束她要去上班肯定來不及——當然也可以請假,但如果可以她還是想好好保留自己的特休,一年可以陪手塚飛出去個幾天,她也能看個幾場現場比賽。
比賽準時開始了,對著小小的螢幕,由衣捏著手心,小小聲地歡呼或驚呼。
連線的是國外的轉播網站,賽評說些什麼她其實聽不大懂。
與其說她在看網球比賽,她純粹只是在看場上的那個人閃閃發光的模樣。
有的時候,這樣看著又會有些哀傷。
鏡頭切近,畫面雖不清楚但由衣知道手塚把結婚戒指摘下了。
在比賽中這是必然,但她常常恍惚覺得裡面的那個人不是她的枕邊人。
她其實可以選擇作為一個可以陪伴丈夫四處比賽的家眷,畢竟家裡並不缺她一份收入。
但可能還是有些傲氣的吧?
從以前就是這樣,她常常想著要怎麼樣才能堂堂正正地站在手塚身邊?她是不是被手塚需要著?她也想跟手塚一樣在某個屬於她的地方閃閃發光。
因此她還是想暫時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拚出一些什麼,選擇了目前的生活。
不過,她也知道未來的某一天,她還是會選擇待在離他最近的地方。他去哪,她就要去哪。
恍惚了一下,手塚拿下了決勝分,比賽結束了。
窗外天濛濛亮,由衣伸了一個懶腰。
轉播來到了場邊訪問的部分,由衣想著反正也聽不懂,正準備關掉電腦時,忽然被畫面中的手塚的動作吸引住。
他臉上依然平淡無波地回答著問題,但同時間他似乎將某個東西往手指上套,然後手便自然垂下到畫面捕捉不到的位置。
一直到直播結束,由衣都沒有機會看清。
由衣下意識地撫摸著自己手指上那一只相同款式的結婚戒指。
她稍早確信著手塚比賽中是沒有戴戒指的,而現在即使沒有看清,她也確信著那個動作是他將戒指套回去了。
就在比賽完的當下。
心頭感到一陣悸動,她感覺自己現在的喜悅比起剛剛手塚獲勝的瞬間還要多出許多。
這次去接機的時候,久違的不畏人群,給他一個大擁抱吧!
她聽到自己呵呵傻笑的聲音。
6.依舊無法拒絕的撒嬌
手塚國光是一個有原則的人。
任何時候,他從來都是從理性的角度出發去面對每一件事。
他很清楚由衣的性格,包含她討厭什麼。
所以他實在不太明白為什麼有時候她會提出某些可行度極低的要求?
比如她討厭人多,她總是在人潮擁擠時緊緊拉著他的手,緊皺著眉頭想快些到能呼吸的地方。
比如她討厭長時間的步行,從學生時期即使他們會去登山健行,由衣也總是在半路就各種耍賴表示抗議。
比如她討厭過於華而不實的物品,購物時她會選擇外貌與實用度兼顧的那一樣,或是實用度更高的那一樣。
可是她總會撒嬌的說她想去賞櫻、想去煙火大會、想去賞楓、想去新年參拜。
她也會找出很多風景優美但行程相當考驗體力的地點說著想跟手塚一起去看。
經過花店的時候,她也會嘟囔著如果能收到鮮花該有多好?
「新年的第一個日出?」手塚雖然表情沒有變化,但語調不如平常的平穩。
「嗯!對呀!再過幾天要過年了,我們沒有一起看過新年的日出吧?我知道一個私房景點喔,不用人擠人!」由衣興高采烈的打開手機,「就是這裡。」
那是附近郊區的位置,並不算太遠,是地勢偏高的地方但他記得道路還算寬敞也有路燈,只是需要從巴士站步行不短的時間。
那不是他的妻子會願意步行的距離,何況可能有坡度。
「你覺得怎麼樣?一起去嘛!」由衣勾住了他的手,眨了眨眼。
要趕上日出,出發時間一定要很早,由衣的起床氣在冬天尤其嚴重,光是起床她可能就要掙扎許久。
但這是她的提議,若當天讓她繼續睡,她也會在錯過時間後埋怨。
「你怎麼不說話?你不願意嗎?可是我真的很想看一次,我保證,我會乖乖自己起床,好不好?」由衣不死心的晃晃他的手臂,聲音柔軟,有些可憐兮兮的。
即使起了床,那段路程她一定會後悔,彷彿也能想像她跟不上自己的腳步而無理取鬧的模樣了。
他不太擅長安撫理智斷線失去邏輯的由衣,光想就有些頭痛。
怎麼想都應該要拒絕這個提議。
他卻說不出拒絕的話。
「嗯。」
「好耶!國光最好了!」
7.鐵樹也會開花
由衣覺得自己可能在作夢。
踏出公司門口時,她幾乎是馬上就發現了佇立在門口的那人是誰。
跟她一起出公司的同事困惑的看著她:「嗯?由衣妳怎麼了?」
聽到這個聲音,那人回過了頭,朝向她走來。
他禮貌的向由衣的同事微微點點頭,然後又看向由衣開口:「我來接妳。」
由衣不敢眨眼,生怕自己出了幻覺,還是她的同事低聲驚呼:「哇!是妳老公嗎?好貼心!」
這才讓她知道她不是做夢或是幻覺。
於是她終於眨了一下眼,點了點頭。不知道她是對手塚、還是對同事。
但總之,她就被手塚牽著離開了現場。
她應該還是有好好跟同事道別吧,如果沒有,那就明天再道歉好了。
不過手塚並不是帶她回家,而是去了一家有些高級的餐廳。
因為今天是她的生日。
從他們認識到如今這麼多年來,他並沒有幫她慶祝每一次生日,但只要他有幫她過生日,她都能感動到抱著這個回憶開心很久。
吃了一頓豪華的晚餐後,手塚還帶著她去不知道是做什麼活動所以掛滿燈飾的商店街。
她一路嘰嘰喳喳地說著沒想到今年你能幫我過、晚餐很好吃、商店街的哪間店賣的東西都好可愛云云,手塚都一如往常的簡短回應。
散步了一段時間,晚餐喝紅酒的酒勁上來了,他們便一同搭車回家。
回到了家,由衣有些暈眩,脫了鞋就撲向了沙發,情緒還是相當高昂,喃喃的說著:「今天好開心唷。」
沒注意到跟在她身後的手塚從口袋中拿出一個天鵝絨的盒子。
「由衣。」
「嗯?」由衣直起身體,臉頰紅撲撲的。
「生日快樂。」
手塚將盒子遞給她,由衣有些驚喜。
「是什麼?」
「耳環。」
「幫我帶上嗎?」由衣打開盒子,是一對小巧的銀製貼耳式耳環,造型是她喜歡的百合花。
手塚沒有說話,默默地撥開由衣長髮塞在耳後,然後將耳環帶了上去。
在手塚的手離開自己耳垂時,由衣勾住了他的脖子,然後在他臉頰上輕輕一吻。
「謝謝你,嘿嘿。我不貪心,我覺得你這樣就很好了。」
吃晚餐、約會、送禮物,雖然在一般情侶或夫妻來說再常見不過,甚至如果以由衣對於「浪漫」的標準來說實在過於普通了,但她很清楚這是手塚重視這一天的最大表現方法了。
她喜歡他的心意。
由衣腦袋有些沉沉的,正想鬆手,就聽到耳邊傳來的鼻息聲有些像是輕笑。但她剛好垂下眼瞼沒看到手塚的表情,難道她又錯過這個面癱難得的笑容?
「要更貪心些也無妨。」
她依舊看不清手塚的表情。
因為她閉上了眼。
接著,她感受到自己被她的丈夫的氣息籠罩了起來。
8.只向你坦承的軟弱
手塚意外受傷了。
只是場小賽事,賽程也沒有因為這樣而被中斷,他也在由衣抵達之前將比賽比完並且拿到了勝利。
之後的幾天他仍會留在原地休息,由衣到飯店的時候正巧他接受完治療,並且與球隊的醫生討論完狀況。
她風塵僕僕的趕到時,手塚就在飯店大廳等她。
「你怎麼樣?」由衣緊張的看著手塚左臂上的彈性繃帶。「嚴重嗎?」
她已經不是十幾年前那個看到因肩痛跪倒的他而被震動到無法有任何反應的女孩了。
「……先上樓。」
「嗯。」由衣拒絕了手塚自然伸過來要幫她提行李的手。「不重,我匆匆來的,只帶必要的衣物而已。」
手塚頷首,領著由衣上了樓。
比起以前手塚總是做出讓由衣匪夷所思的選擇,如今的他謹慎多了。
再來就是運動員難免會有些運動傷害,即使手塚常常超出那個範圍,由衣待在他身邊久了也習慣了。
進房間放下物品後,由衣拉著手塚坐下。
「怎麼樣?要休息多久?要注意什麼嗎?」
「只是前兩天痛得比較厲害。」
由衣嘆了口氣,老成的就像平常的手塚。
「那就好,還好比賽也結束了,你就安分幾天不……嗯?」
手塚伸出右手將由衣拉近了些,還沒等他變換姿勢,由衣就自行伸手圈住他的腰,靠在他胸膛上。
「你怎麼了?」
「想到了前兩天手臂舉起來覺得有些困難的時候。」
「哦。」
由衣閉上了眼睛,聽著他的心跳,不如平常平穩。
莫名地想起那一年她去九州,看到他毫無進展的復健過程,以及那藏不住的眼神中的焦急。
那時的他還會鎮定自若地對她說放心。
「但現在沒事了對吧?」
「嗯。」
她更喜歡現在的他。
9.憶起當年
他們夫妻都有買書的習慣。
一開始家裡就規劃了很大的書櫃,即使如此,以他們的藏書量,也經常要整理調整位置。
除了書房的書櫃牆,客廳裡也有兩三個簡易的拼裝置物櫃,經常翻閱的書籍雜誌會放在那裏。
手塚要將過舊的雜誌整理出來時,無意間瞥見了幾本厚厚的相冊。
在數位時代,這樣的相冊也很少見了。
雖然由衣有時會將喜歡的照片自行列印出來保存,但數量上確實也比起過去只能沖洗照片的年代比少了許多。
他心血來潮的將相冊拿出來,發現是學生時期的相冊。
這本是由衣的高中時期照片,那是他所缺席的時期。
仔細想想,他其實經常在由衣的生活中缺席。
就算是結婚了,還是不比中學那三年的朝夕相處。
——不,即使是當時,也還是有他去九州的那一小段空白期,對於成年的他們來說不是太長的時間,但對於中學生來說就不一樣了。
但空白最多的時候還是在他們真正成年前的那幾年吧。
他記得因為他去了德國,由衣考上了一間以她原本的偏差值來說非常勉強的私中,就為了那間學校在高三時能爭取去德國交換學生。
雖然他並不在她身邊,他知道當時除了課業以外,她也擔任幹部希望增加積分,另外還去打工存錢希望減少家裡負擔她出國的生活費。
但最後她沒有去成。
她總是這樣,用盡全力追在他身後。
一開始她會說,我跟不上你了。
後來,她只會咬著牙前進。
他翻開了相冊,當然高中的那三年他也有回日本,也不是完全無法見面的狀態,但照片裡的由衣確實讓他覺得陌生又熟悉。
要說遺憾嗎?倒也不至於。
畢竟她也的確一直都在他身後,或是身側。
「你什麼時候喜歡我的?為什麼喜歡我?」由衣曾經在他平舖直述的表達自己心意後,忍著害羞這樣問他。
他只覺得經常說他遲鈍的由衣才是真正遲鈍的那個人,而對這個問題無奈地嘆息。
她怎麼會覺得「喜歡」會像開關一樣,某一天因為條件滿足而切換過去就叫做喜歡了呢?
至少對手塚來說他對由衣的這份情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
「你在看什麼啊?」
由衣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他還沒回答,由衣就高聲地說:「哇!是高中照片!好懷念喔!」
她湊了過來,明明是自己卻也饒富興味地看著。
翻了幾頁,手塚注意到有個少年經常出現在由衣身側。
「這是妳的朋友嗎?」
「嗯?」由衣仔細看了看,然後露出狡黠的笑容:「算吧,因為他沒有追到我。」
「……」
「其實你應該見過耶,因為有幾次你回來……噢,還有我們學校文化祭時你也有來不是嗎?」
他確實不太記得由衣身邊有這樣一個人,陷入了沉思。
「反正畢業後也沒怎麼聯絡了啦。」由衣無所謂地說,「不過當時他算是幫我很多吧,畢竟那時候年輕嘛,你可要知道喔,十幾歲要談遠距離戀愛是很難的。」
很難?
手塚又深深皺起了眉頭。
「嘿嘿,你不知道吧!」由衣低聲笑了笑。
「那時妳覺得很辛苦?」他知道當時由衣經常因為思念而心情低落,但他沒想過或許由衣的難過比表現出來的多更多。
「嗯……你現在問我,我當然覺得還好。但當時——交換學生資格確定爭取不到的時候我是真的覺得世界末日了。」由衣歪了歪頭,補充道:「畢竟我還是比較屬於希望能一直待在戀人身邊的類型吧。」
話題就這樣嘎然而止,由衣也不太在意。他們沉默地又翻了一下,翻完之後手塚把相冊收起,由衣也起身進了廚房。
手塚完成了原本在做的事情,看著廚房內的由衣,思索了一陣子。
「現在呢?」
「啊?」由衣停下手邊工作回頭,一臉困惑。
「妳覺得辛苦嗎?」
「有一天我應該還是會放下一切待在離你最近的地方吧。」由衣笑了笑,「現在好很多了,至少我能選擇了。」
也許有一天,會是他停下腳步留在她身邊吧。
10.「歡迎回家。」
這次的比賽由衣無法來到現場。
其實對他來說,他一樣全力以赴面對比賽,他也很清楚他的妻子絕對會不管時差選擇看轉播。
雖然他不喜歡她熬夜,想看比賽也可以選擇先錄影起來看重播,但是她總是陽奉陰違。
天高皇帝遠,他也確實管不到——畢竟在身邊的時候也未必能管到。
在場邊準備時,他摸索著左手無名指的婚戒,將它摘下,放在他的運動外套的一個內袋,謹慎的拉上拉鍊。
這是他結婚後多出來的賽前準備動作。
現在時間,日本應該五點了吧,如果由衣有對抗睡魔成功的話此時應該在看直播了。
「請選手入場。」
提起球拍,他踏入了球場。
每一次的比賽無論對手強弱,他都是全心投入求勝。
這次也不例外,他打出了一場讓賽評球迷都為之瘋狂的精采比賽。
取得勝利後,他喘息著來到場邊,簡單的喝水擦汗後被指示到場邊接受訪問。
他提起運動外套,熟練的伸入內袋拿出結婚戒指,場邊訪問人員已經就位,他一邊聽著問題,一邊將戒指套上。
彷彿就像呼吸一樣自然。
後來由衣是在這邊時間的隔天早上才傳來祝賀訊息,他也如同往常一樣回覆她回國時間就結束訊息的往來。
雖然比賽已經結束,他總是有些靜不下心。
一開始遇到這個情況時不太明白,幾次之後他大約知道原因了,這個變化也是在結婚後才產生的。
原本只要一通電話、一則訊息就好,如今的他或許也變貪心了。
由衣在見到他的第一眼,就開心的撲了上去。
雖然沒有準備,但他還是反射性地穩穩撐住了由衣的身體。
「怎麼了?」
由衣稍微放開他,抬起左手,然後指了指無名指,「我很開心。」
手塚不明就裡,只是在由衣又撲上來的時候不只撐住而是回摟住她。
「國光,歡迎回家!」
「我回來了。」
於是他靜下心來。
2023年5月9日 星期二
Blue Snow - 第二十八章
玫紗緹思三人被這位熱情的大嬸帶到一處小屋,屋外簡單圍著一圈圍籬,有一個地方不大的小菜園,只不過因著季節似乎正休眠中。一旁的簡陋羊舍養著一對白色的山羊,正懶洋洋的嚼著乾草。
「來吧,雖然我這簡陋但進來取取暖吧。我來找找有沒有能給你們替換的衣服。」
事實上依希爾跟艾諾爾有辦法馬上處理掉身上的濕衣服,但在外面世界他們也不想如此輕易使用魔法以免難以解釋,只好笑著道謝。
屋內升著小小火盆,大嬸先是拿了兩套外衣,然後拉著玫紗緹思進了裡間。
伊希爾從善如流的脫去自己的大衣,套上了其中一件深藍色的羊毛外衣,一邊說:「也幸好遇見了人,還可以問問看這裡是哪裡。」
艾諾爾則是穿上深棕色的外衣,「看起來這附近好像也沒其他農莊了,但大嬸生活所需總需要採買吧。」
「待會再問問吧。」
玫紗緹思換了套淺藍色的裙裝,外加一件白色的對襟羊毛背心。頭髮還有些濕轆,她用一隻木製的簪子鬆鬆的挽在側邊,添了一些溫婉的氣質。
「大嬸妳這竟有我們合身的衣服?」玫紗緹思攏了攏側邊的頭髮,問。
「我兒子女兒都不在,但還留著些舊衣服便將就了。」大嬸笑得有點寂寞。
玫紗緹思看身上的服裝不太像舊衣服,想著大嬸肯定相當思念自己的兒女,所以保存的很用心,不禁有些同情。
跟著大嬸一同走到外間後,他們一同坐了下來。艾諾爾率先發問:「大嬸您一個人住啊?在這裡不方便吧?」
「家裡人少也說不上不方便,就是現在天氣冷要採買不方便。」大嬸笑了笑,「倒是你們三個,是要去哪裡探親啊?」
「啊,是這樣的,我們三人是要去找許久沒連繫的親戚。在葉凌古平原上的一個小村莊。但我們很小的時候就遷到南方去,村莊名字也不太記得。」
大嬸瞪大了眼,「那你們也真是夠大膽的!從那樣遠的地方要去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艾諾爾轉著眼珠,又想了想,換上有些尷尬的表情,「本來有租馬車、還有地圖。不過大嬸妳看我們也知道沒什麼出遠門經驗,這不是路上遇到騙子就沒了車,連地圖都弄丟了。好在我們貼身帶著的旅費沒有完全被騙走。」
伊希爾斜睨了艾諾爾一眼,他真不知道自己的弟弟說起謊來能夠如此自然。在心裡暗自想著未來他所說的話應該都必須打點折扣。
善良的大嬸點點頭,看上去有些憐愛,「唉唷真是可憐!葉凌那邊我倒是聽過,那裡有很多從古老的世紀就存在的部族,聽說還有會吃人的!你們根本就是衝進獅子嘴裡的小羊!我可從沒聽過那邊有什麼村莊!」
「唉呀,那真的太謝謝大嬸提醒了!如果大嬸能告訴我們最近有人煙的城鎮就太好了,至少我們能買張地圖,或是跟那邊的人打聽看看!或者不是在那個平原上,而是週邊?或是名字相似的地方呢?」艾諾爾打蛇隨棍上的繼續說。
「我平常會往來的就是西北邊的德里斯,那邊來往商旅多也方便。要打聽事情去那邊最好不過了。但——」大嬸望向窗外,「瞧,下雪了。」
三人跟著望出去,果然不知何時已經細細飄起雪花。
「今天你們都受了涼,還是在大嬸這邊歇腳一天吧。不要再去淋雪了。」
「不行的,這樣太麻煩大嬸您了。」玫紗緹思急急擺手。
「別跟我客氣了。反正我一個人也怪無聊的。」大嬸揚著親切的笑容,「我叫達歐倪,你們叫我達嬸就行了。你們的名字呢?」
「這……」依希爾有些猶豫,不過艾諾爾拋了個眼神過來,他意會的點點頭。「那就麻煩達嬸了。」
於是三人各自報上姓名,便乖順的留了下來。
*
「噯,今天的青菜怎麼又貴了些?」婦女提著菜籃,皺緊了眉頭。「昨天一個銅幣能買一大把,今天怎麼就少了一半呢?」
蹲在地上的菜販抬頭賠著笑臉說,「這不是最近才剛安定嗎?新國王昨天又發了新的稅令,我家那畝田又被補徵了不少稅金呢……」
「好吧好吧!」婦女嘟囔著這年頭可真難過日,不過在這四季如春的島上,農產品的價格波動已經算是最小的了。起碼再如何都不會因為氣候而影響產量。她不甘不願的掏出第二顆銅幣,「那再給我一些吧。」
菜販高高興興的伸出了手,但落入他手中的卻是另外一枚銅幣。
「抱歉,大姊,跟妳打聽點事,這菜錢做為我一點心意。」男人穿著一件長斗篷,帶著兜帽,雖看不清他的眉眼,但從他下巴剛毅的線條來看卻不是太過難看。他的聲音也柔和地如金妮島上長年吹著的微風般溫柔舒適。
「唉呀,這時節有外地人來真稀奇。」
男人輕笑,「早些年我曾來這做過生意,很喜歡這裡。只是今年再來,發現有些不一樣了。」他遙指城堡上的旗幟,「那不是國王的旗幟吧?」
婦女有些緊張的壓下他的手,「那是你不知道,你若是前幾年來過,那我告訴你,如今的國王是當年的西芮爾公爵,可別這樣亂指。」
「……抱歉、抱歉。」男人停頓了一會又笑,「這,我還以為前國王還當盛年,難道……」
「前國王倒是還活著,只是被流放了。」婦女平日裡就愛說些八卦,看到有個搞不清狀況的外鄉人她自然抓緊了機會滔滔不絕:「這幾年啊,因為前國王老愛出征,打了幾個小國下來後更變本加厲擴充軍隊,結果弄得我們一般老百姓生活辛苦,家裡能做事的男丁也都被推去戰場。之後又是徵糧又是徵地,西芮爾公爵便組成聯軍推翻了他。」
「哦?但我記得前國王手下有個驍勇善戰的大將軍,怎麼也抵擋不了嗎?當年他不也是倚靠這個將軍跟幾個貴族一起聯合拿下了政權?」男人說話時彷彿壓抑著什麼,「當然了,當時的政權也腐敗不堪,據傳當年的繼承人又是個紈褲不堪大任,王者,自然是有能者居之。」
「唷,你還知道艾特將軍啊?」婦女神秘兮兮笑道,「雖然我不知道詳情,據傳——當日帶頭逼宮的就是艾特將軍呢。雖然很多人不太相信啦!畢竟艾特將軍跟前國王是自小的朋友。但如今是新政權了,艾特將軍仍然還是大將軍,我看這謠傳根本是事實!」
男人愣了一下,嘴角的微笑有些扭曲,看得這婦女有些緊張。
「喔對了,前國王流放了,王妃呢?」
「反正你只是個商人,問那麼多幹嘛?前國王都不在了,王妃能去哪?」菜販擺擺手插嘴打斷,「對了,你們也別老站在我這攤子前面,我還要做生意呢。」
婦女沉了沉臉,剛剛為了賣菜還賠著笑臉,現在就翻臉不認人了,看她之後還買不買他的菜!
男人先是溫和微笑道了聲歉,轉頭又向婦女說:「謝謝這位大姊了,咱們也別打擾老闆了。我這就告辭。」
婦女應了一聲扭頭又往麵包店的方向而去,而這個文質彬彬的男人則是若有所思的慢慢踱步遠離。
沒人看見他藏在斗篷下的手捏緊了拳頭,並有一道綠光閃了一下。
2022年10月30日 星期日
【復甦島二創】【志美】陪伴
35年了。
他見過那樣多的人、了解人性的黑暗與光明,從沒有在任何賭注上失敗,更甚於幾乎沒有因為無法掌握、無法控制、無法預知而恐懼過。
但那名少女打破了一切,所有他認定的規則不復存在。
起先,他以為她跟所有人是一樣的。
他如過往一般斯文有禮、溫柔的對那個失去記憶、沒有過去與親友的少女微笑。即使那名少女眼中閃著狡黠光芒、用天真爛漫的語氣說著歪理從他手中誆走了一些小錢他也沒有對她發怒。
所以,少女短短的日子內就對他產生依戀,是必然的結果吧。
錢,什麼都可以買到。
「沒關係啦美美,我會保護妳。」
「我可以保護自己!」
他總是沒有注意到那名少女胡鬧語氣下的堅定。
因為她橫衝直撞、不明白現在的世界有多麼險惡;因為她即使沒有過去的一切,也被「他」與他的隊員、以及高聳的高牆保護著;因為她恰好身邊都是同樣受著保護、既善良又體貼的鎮民們。
光是與人相處她都需要他從旁斡旋了。他想。
所以,當她說:「能保護自己。」對他來說,就像小孩的賭氣話一樣,不值一聽。
而後來,這名少女讓他第一次體會差一點賭輸的感覺。
不過是戲言一句要讓美美開車而已,卻讓他一瞬間以為自己生命要這樣不明不白的終結了。
或許那就是個徵兆吧,在提醒著他這名少女將會如同這次經驗一般帶給他過去不曾體驗過的「不確定」。
*
你好,我叫黃美美17歲D罩杯。
來到這個由高牆圍住的城鎮之後她逢人就這樣說。因為這是她僅存的一點點記憶。
雖然生活自理沒有問題,但對於過往以及這個變異的世界她是相同的茫然。
她並不知道什麼叫做「正常」,但隱隱知道這個世界現在這樣好像不怎麼正常。
那個男人,她也不過是見他笑臉迎人覺得親切,就臨時起心動念要他陪她一起去釣魚。
她不懂那張笑臉其實是男人畫界線的方式。
「大志哥哥!」
她撒嬌般的這樣喊,但其實任何稱呼用她甜美的娃娃音喊出都是那樣柔軟。
「我的錢包跟衣服都不見了。」
「好啦我陪妳去找。」
無論她遇到什麼,那個男人總是很有耐心的陪著她。
她並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但她知道她希望那個男人能一直陪著她。
然後如同本能一般,她也傾她所有的回報他曾經賦予她的——無論真心與否的溫柔。
那一天到來。
她有記憶以來村莊內最悲慘的一日。
村長死了、麥麥死了。還有好多她不認識的自治隊隊員也死了。
大家哭成一團、亂成一片。
但比起其他人,她更在意那個男人。
呂志一向讓人覺得堅毅的背影看上去變得單薄。
他滿臉掩飾不了的疲憊,他再也無法游刃有餘的對她微笑。
她能做些什麼?
*
他不信神,因為他很清楚教會是用什麼方式維持信仰。
教主維持信仰可以凝聚鎮民向心力,而實際出力守護高牆鎮的則是他,他很以此為傲。
不容許任何差錯。
無論是自治隊破壞紀律、或是布好天羅地網要將紅圍巾一網打盡卻變成折損四名隊員的事,都不該發生。
但這些事情卻接二連三的發生了。
事後想想,那就像雪崩一樣,一開始只是一點點,但轉瞬災難就到來了。
所有事情在那天失去了掌控。
他必須向外來者低頭求助。
他跑向敞開的大門只見隊長帕奇的屍體。
他奔回應該相對安全的雜貨店卻聽到村長已死。
他還沒搞清楚這一切為何發生又聽到自己的隊員倒了三個在教堂內。
「你不用去,醫生已經看過了,那沒救了。」
教主失蹤了、許多人死了、不僅大門毀損高牆也破了大洞。
他的驕傲蕩然無存。
心理跟身體都疲憊到了高點,他無法再分出多餘的心力到少女身上。
「美美,我可能不能再顧著妳了。」
「我只是怕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卻不開口。」
「那美美,我現在希望妳能保護大家。」
「好,我知道。」
她堅定地對他點頭,看見她眼中閃著的光芒,他終於知道那不是賭氣話。
他終於知道這名少女根本不是他一開始想像的那樣。
*
正常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其實即使是疫情前,他也不是在什麼很正常的環境下長大的。
所以他其實無法想像什麼叫做正常人、普通人。
他只會他原本的那一套生存方式。
但在村莊慢慢重建的過程,在看到那名少女獨立起來為了大家奔波的模樣,他忽然有點嚮往起來。
他忍不住開始想像起「普通的生活」。
那名少女超乎他想像的堅強,他以為她會像冉冉或戚栖那樣無助哭泣然後慢慢振作。
但她彷彿沒有低潮一般,僅僅是在此刻出錢出力的去做任何一切她做得到的事情。
那名少女哭喪著臉說:「我昨天種的東西都不見了。」
儘管在此之前少女哭訴過無數的芝麻小事,他表面耐心回應心裡也只是冷漠以對。
但這一次,他忽然有了一絲絲的愛憐之心。
於是趁著少女不在,他去問了奇恩店長圍欄要怎麼做,並且一人默默地開始砍樹、鋸木板。
或許這是他第一次真心的、為了讓那名少女可以笑起來而去做一件事吧。
而他也發現自己由衷的希望,那名少女可以繼續開心的笑著過每一天。
所以,他以自身作為賭注,他從來沒有這樣賭過自己。
賭一次成為普通人的機會。賭一次給其他人能安穩生活的機會。
「等到一切結束後,我將會辭去自治隊的顧問。」
*
她沒有見過戰場,她也不知道真槍實彈是什麼樣的。
但她想,也許他們在這一天要跟那些有作戰經驗的人一起提起槍去面對可能更強大的火力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也說不定。
但她執拗地想遵守她與呂志的約定。
說好了,會保護自己。
說好了,要幫忙保護大家。
即使拿著槍的手不斷顫抖、即使響在耳邊的槍聲震耳欲聾。
她還是固執的前進。
即使穿了裝備,也很難在這樣的戰場上全身而退,她覺得渾身痛得要死,但還是堅持跟在呂志身邊。
她也見識到了這樣的戰場不比牆被炸開那一天還要好到哪裡去。
一片混亂下,死的死、重傷的重傷,她不可能完全無動於衷。
但心底還有一絲絲慶幸吧。
她跟他,終究是在那場槍戰下倖存了。
最後只剩下一件事,而對方的人也死傷慘重不會再威脅高牆鎮了。
帶著人質換回教主,一切就結束了。
即使不是那樣圓滿,終究是平安了。
應該要是這樣的。
「那就只好把你們殺掉!」
那穿紅衣的身影詭譎迅速,而他們已經太過疲倦。
「等一下!」
在她反應過來之前,她看到自己身上噴出了跟那紅衣身影一樣的,鮮紅的液體。
在痛楚席捲而來之前,她已然被黑暗籠罩。
「美美!妳有聽到我說話嗎!美美!」
——「我會保護妳。」
失去意識之前,她想起了許多。
每一個記憶片段,都有那個金髮男人。不管其他人怎麼看他,那就是她認定的、世上最溫柔的人。
原來,他們陪著彼此走過的日子那麼短又那麼絢麗啊。
她想,她睜開眼睛後一定會用最戲謔的笑容逗著他說:「好像是我在保護大志哥哥耶。」
如果她能醒來。
*
他手上沾滿鮮血不是第一次。
但那不應該是她的血。
數不清了,他說過了幾次會保護美美?
什麼教主、什麼Uncle、什麼萬能細胞?
重新建立信仰?讓高牆鎮恢復和平?
他到底為什麼提起槍來到這裡、為什麼要帶著大家來到這裡、為什麼要叫她跟緊自己?
「我連美美都保護不了我還想保護什麼高牆鎮?」
他早就沒有了驕傲,從高牆無法庇護所有人的那一天起就沒有了。
所以他任由看似弱小的村民們一個一個拿起刀槍、穿上裝備前進戰場,他早已認清自己無法守護每一個人。
但他不知道的是連一名少女、一個雖然起頭莫名其妙,但後來悄悄在他心中占據一角的少女,他都無法保護。
原來他是這麼無能。
「不然醫生我的血可以嗎?要抽多少都可以。」
一命換一命。
世間才沒這麼好的事,他怎麼會不知道?
他怎麼會不知道他能做的努力是這麼少?
當他雙膝落地時,他想說的是什麼?
是對不起?還是求求你?
不信神的他,又能夠對誰祈求呢?
*
「美美?妳醒了?」
他的聲音好像帶著一點微弱的哽咽,好像第一次聽到他那樣子說話。她知道他很溫柔,但她第一次感覺到那份溫柔帶著溫暖。
呂志告訴她,她已經昏迷了五天。
而且他守了她五天。
她忽然意識到自己現在蓬頭垢面,急著想把自己打理乾淨。
「我現在是不是很醜!我要去找花口院老闆!」
他堅持陪著她。
好像以前都是她堅持跟著他。
他依然走在她斜前方,她想,如果她上去牽他的手,他會不會掙脫?
但無論如何她不能再這麼醜下去了!
她是美美,她應該要一直都美美的。
*
高牆鎮以後要怎麼走下去,好像對他也不重要了。
反正他是普通人了。
從現在起他也只想真心的關心並陪伴想陪伴的人,真心的。
她醒來了,陪在他身邊歡笑。
他會任由她依戀的看他、任由她肆無忌憚地開他玩笑、任由她占盡他的便宜。
「之前你不是說當顧問不能談感情嗎?」
「現在可以啊。」
「那你要我開口是不是?」
他回頭看她一眼,她眨著眼看他,棕色的前額髮遮不住她眼裡的光芒。
「那……妳願意,跟我這個普通人一起生活嗎?」
「我考慮一下。」
她抬起頭對他微笑,呂志看清了美美眼中閃著的光芒——狡黠的、充滿笑意的、帶著愛戀的。